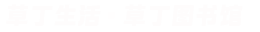有学者指出,要鉴别真伪,关键在于搞清《清明上河图》别本产生初始的情况,及其历史流传的脉络,方能还各本以历史本来面目 。 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,《清明上河图》别本最初发现于元代,当时有“秘府本”与“似本”两幅 。 当时,杨准跋文中称:“图初留秘府,后为官匠装池者以‘似本’易去 。 ”就是上面说到的元代时,装裱匠以临摹本偷换了真迹,这临摹本后称“似本”,实为元代作品,显然是赝品 。 到了明代,又出现张英公收藏的“稿本” 。 王世贞《弁州山人四部稿续稿》卷一六八《清明上河图别本跋》说到,张择端的“稿本”,“于禁烟光景亦不似” 。 清明寒食,民俗禁烟,“不似禁烟光景”就是说画得不是清明时节,或许是张择端此画的早期手笔 。
先来看台湾的《清明易简图》 。 沈德潜《清明易简图疏解》记:“张择端清明画图,本有二幅,一在张英公家者,名《上河图》,有张著跋;一留汴京者,无跋,意即《易简图》也 。 ”沈氏明确告之,《清明易简图》是张公英所收藏的“稿本”之外的另一本《清明上河图》 。 而“秘府本”真迹如果在明末的灭顶之灾中失传,那么《清明易简图》最多是元代的“似本”,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(1295)首跋《易简图》时,就开宗明义道:“清明易简新图成 。 ”说明它是新近画就的,图中还可见一些元代事物:如元代独有的官方文化机构“奎章阁”,棉纺技术经黄道婆改良后才传到北方的“吴淞细密花布”等 。 所谓张择端的亲笔题款一事,实是不可信的,主要是“翰林画史”之称,宋画院并无此官称;刘渊临把张择端称为金人,而金朝也无此官称 。 尤其是其画上还有“金太祖题字”,从时间上就可看出这在作假,所以清乾隆题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盖出于庸手妄作 。 ”尤其是整部画的风格,经仔细比较,与宋代画院风格截然不同 。 所以判断台湾的《清明易简图》基本是赝品,至于是元代作品,还是明代作品,学术界还有争论 。
再看北京故宫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除了上述题跋、印鉴、画风诸证据外,其画面上却出现了扇子、西瓜、新酒、光身儿童、遮阳草帽等显然是秋天的景色,恰如上述“于禁烟光景亦不似”的特点,那就有可能是“稿本” 。 此画还不见有宋徽宗瘦金体的签题和他的双龙小印之印记,那么是因为此“稿本”没有呈现给皇帝,还是年代久远,赏玩时时磨坏而在装裱时被裁割了呢?然而也有学者不同意它描绘的是秋景(详后谜),并认为它就是真迹 。 指出判断真伪几个关键是:一看城墙画得如何?宋代东京的内城与外城均为土墙,只有北京《宝笈三编》本画的是土墙,其他各本均为砖墙 。 二看虹桥画得如何?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载,此桥是木结构的单孔桥,“其桥无柱,皆以巨木虚架……宛如飞虹” 。 也只有北京《宝笈三编》本属于这一桥式,其他图本均为大型单孔石拱桥 。 三看城楼画得如何?北京《宝笈三编》本仅画城楼,并无瓮门,类似东京内城之制;其他图本均有瓮城,不符合东京外城之制 。 四从绘画风格上看,只有北京《宝笈三编》本符合宋代画院的笔法 。 以上诸点,可以证明北京《宝笈三编》本就是张择端的真迹,不过这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。
关于美国纽约收藏的“元秘府本”,董作宾进行了详尽考释,根据徽宗瘦金体题跋,认定该图是张择端“宣和二年七月”之前进献皇帝的真迹 。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晚期赝品,其题跋与别本往往有些许不同,但也难辨真伪 。 学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研究成果,对台湾、北京、美国纽约三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,最后还是不敢肯定哪个是张择端的真迹 。
推荐阅读
- 学习知识|潜怎么读,是什么字?
- 学习知识|雄怎么读,汉语拼音是什么
- 学习知识|晨怎么读,晨是什么意思
- 九成新的意思和区分方法 九成新是什么标准
- 椒盐的的做法和用途 椒盐是什么调料
- 乌日莫的做法和保质期 乌日莫是什么东西什么味道
- 荷花烟系列介绍和价格表 荷花是哪里产的烟
- 消毒和消杀的区别及常见消毒方式 消杀是什么意思
- 娱乐知识|顾雨薇l先生是谁
- 娱乐知识|kmr是谁,kmr为什么是神